令人痛心的校車事件頻發,“撤點并校”這個原來公眾并不熟悉的教育詞匯迅速引起大家關注,一些輿論分析,不恰當的“撤點并校”制造了當前的校車困境。而前不久開始征求意見的《校車安全條例》提到解決校車問題的一條措施是,“調整學校設置規劃,保障學生就近入學或者在寄宿制學校入學,縮短上學距離,減少交通風險。”很顯然,也間接承認“撤點并校”增加了學生的交通風險。
其實,在全國數十萬小學被撤并已成定局之后——僅自1993年到2008年的15年間,我國小學學校已由69.67萬所銳減到去年的30.09萬所,銳減了56.8%——再來談“撤點并校”的問題,以及糾正“撤點并校”的做法,用“亡羊補牢”來解釋,都解釋不太通。
鄉村學校的“撤點并校”,早在這一政策推出時,就遭遇質疑。雖然政府部門解釋這是農村生源減少的必然選擇,一些自然村上學的孩子銳減,當地的學校招生嚴重萎縮,而且有著諸多好處,比如整合鄉村教育資源,(讓村上的孩子到城鎮求學)提高教育質量。但是,很多鄉村居民并不買賬。具體原因包括:孩子上學路程遙遠,上下學花在路上的時間太長,存在嚴重的交通安全隱患,上學成本增加,與此同時,合并之后的學校教育質量并沒有提高,本來的“小班化”教育被“大班化”,甚至“超大班化”替代。一些地區的村民甚至以自辦學校的方式來抵制撤點并校,但是,眾多鄉村學校,還是被“強制“撤并。其間,幾乎每年都有相關的新聞報道。
“撤點并校”的負面作用隨著這一政策的推進持續發酵。比較顯著的問題有四:其一,一些鄉村地區出現輟學率回潮,上學路遠,一些家庭干脆不讓孩子上學了;其二,校車問題日益突出,由于政府沒有在撤點并校時考慮配備校車,不少孩子只能坐不合格校車、黑校車上下學;其三,低齡寄宿在鄉村變得越來越普遍,但由于寄宿硬件條件較差、與寄宿相配套的心理輔導、生活服務沒跟上,鄉村寄宿生存在較嚴重的心理問題;其四,朗朗書生在很多農村消失,農村越顯缺乏生氣。
上述這些問題一直被關注教育問題的學者,和鄉村居民提出,但是,這些問題并沒有引起政府部門的重視,直到2008年,廣東才暫緩強制撤點并校——這意味著此前是“強制”撤并,直到2009年,國務院才對農村“撤點并校”提出要求,要注意從實際出發,防止“一刀切”或“一哄而起”。要求各地要制定三年總體規劃,根據城鎮化發展和人口流動變化的趨勢,促進學校合理布局和結構優化。涉及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的,要在深入調查研究和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的基礎上進行。
如果在“撤點并校”時,就能有這種考慮,該有多好。但恐怕很難。首先,就教育利益來說,在筆者看來,各地政府之所以十分積極地“撤點并校”,在于想由此減少辦學點、進而減少教育投入,更方便地管理學校,根本不是什么提高教育質量,為鄉村學生著想。按照地方政府部門的思路,未來一個縣可能只辦一所小學、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,只要既好管理,又突出“大規模”辦學政績,還攻克了義務教育均衡難題——只有一所學校,何來校際差異?但這不是辦學,而是辦工廠。
其次,我國的教育決策機制,雖說要聽老百姓意見,但聽不聽以及聽了之后采不采納,主導權在行政部門,也就是說,“撤點并校”這種事,只要政府決定要干,就沒有干不了的。福州市臺江區內一所投資1500多萬元,剛剛全部完工的現代化辦工廠。 其次,我國的教育決策機制,雖說要聽老百姓意見,但聽不聽以及聽了之后采不采納,主導權在行政部門,也就是說,“撤點并校”這種事,只要政府決定要干,就沒有干不了的。福州市臺江區內一所投資1500多萬元,剛剛全部完工的現代化小學即面臨拆遷,就充分說明了這種決策機制的運作模式。 輿論把“撤點并校”和校車問題,歸為因果關系,但我覺得,這不是因果關系,而是由同樣的教育利益格局和教育決策機制造成。由政府主導的教育決策,如果只顧政府的“利益”,而不尊重教育規律和受教育者權益,就會出現各種形式的漠視受教育者權益事件。只有改變教育決策機制,給受教育者(家長)參與教育管理、決策、監督、評價的權力,才能讓受教育者的權益得到切實維護。這是撤點并校的教訓,值得解決校車安全問題吸取。 小學即面臨拆遷,就充分說明了這種決策機制的運作模式。
輿論把“撤點并校”和校車問題,歸為因果關系,但我覺得,這不是因果關系,而是由同樣的教育利益格局和教育決策機制造成。由政府主導的教育決策,如果只顧政府的“利益”,而不尊重教育規律和受教育者權益,就會出現各種形式的漠視受教育者權益事件。只有改變教育決策機制,給受教育者(家長)參與教育管理、決策、監督、評價的權力,才能讓受教育者的權益得到切實維護。這是撤點并校的教訓,值得解決校車安全問題吸取。

 您的位置:
山東技校網 >> 菁菁校園 >> “撤點并校”的負面作用
您的位置:
山東技校網 >> 菁菁校園 >> “撤點并校”的負面作用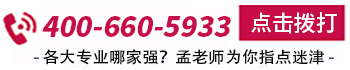
 公安備案號 13024002000224
ICP經營許可證號 冀B2-20170024
網站備案號 冀ICP備11020808號-9
公安備案號 13024002000224
ICP經營許可證號 冀B2-20170024
網站備案號 冀ICP備11020808號-9

